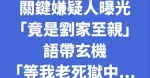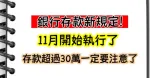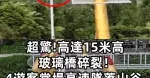5/5
下一頁
三國時代最愚蠢的計謀:魏延子午谷奇謀

5/5
事實上,後來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劉禪的露布天下詔書中就提到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、康居胡侯支富、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」(《三國志·蜀志·後主傳》注引《諸葛亮集》)。支富當是從中亞東遷到涼州的大月氏酋長,康植則出自粟特康國,而當時來中國的粟特人基本上都是商人。所以,雖然這些在涼州的中亞胡人首領稱為國王,且擁有軍隊,但他們的真實身份恐怕還是西域武裝商人集團,他們派人來聯絡、支持諸葛亮北伐,主要還是為了生意啊!
總之,季漢實力弱於曹魏,當以「蠶食」之策由西向東漸次推進,而不是突然鯨吞長安直至潼關。楚漢時項羽遠在彭城,故韓信閃擊三秦乃是良策,而此時曹叡近在洛陽,入援關中非常快捷。所以此一時彼一時也,魏延的「子午谷之謀」太不現實了,甚至連冒險都算不上,簡直就是送死。事實上,這個漏洞百出的計劃或許根本不存在,畢竟,魏延是劉備從基層一手提拔上來的軍事骨幹,整個給人的感覺相當務實,軍事經驗也相當豐富,而且長期駐守漢中,對周邊的地理、經濟情況了如指掌,他怎麼可能會提出這種極不靠譜的計劃呢?
如前所述,陳壽良史也,《三國志》所載原文部分基本可信,但裴松之補註的那些東西卻得打個問號,我們要好好思考一下再決定要不要採納。魏延的這個所謂「子午谷奇謀」,出自曹魏郎中魚豢私撰的史書《魏略》,《魏略》中關於曹魏的史料很有價值,畢竟魚豢是魏帝身邊之人,但季漢方面與曹魏山河阻隔,又是敵國,魚豢能有啥渠道得到季漢高層軍事會議上的信息?而且魚豢後來並未仕晉,他也得不到滅蜀之後晉所獲取的資料。所以這些恐怕只是他道聽途說來的野段子罷了(注10)。這位魚豢,似乎相當喜歡這些八卦,他還在《魏略》中記載說劉禪小時候曾被拐賣過,最後還和劉備上演了一番尋子認親的苦情戲(注11),不去做電視劇編劇真是可惜了。
注1:北方曰子,南方曰午,地理上的「子午線」也是取自這個概念。中國的建築講究中正直,所以秦始皇曾修直道溝通長安至九原長城於子午嶺,王莽則修復蝕中並改名為子午道。還有學者調查研究證實,西漢時期曾經存在一條超長距離的南北向建築基線。這條基線通過西漢都城長安中軸線延伸,向北至三原縣北塬階上一處西漢大型禮制建築遺址(並延伸至秦直道與子午嶺),南至秦嶺山麓的子午谷口(並延伸至子午道與漢中)。這條基線不僅長度超過一般建築基線,而且具有極高的直度與精確的方向性,與真子午線的夾角僅0.33度。由此可見秦漢時期在掌握長距離方位測量技術的基礎上,可能已具備了建立大面積地理坐標的能力。參閱秦建明、張在明、楊政:《陝西發現以漢長安城為中心的西漢南北向超長建築基線》,《文物》1995年第3期。
注2:其實漢中郡治一直在西城(即今陝西安康),直到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,才由從西城遷至南鄭。建安二十一年曹魏攻占漢中,分郡之東為西城郡,而以西城為其郡治,歸當地土豪魏興太守申儀管轄。
注3:詳細分析考證可見嚴耕望《唐代交通圖考》。
注4:據 《三國志·蜀志·劉封傳》注引《魏略》:「太和中,(申)儀與孟達不和,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,及達反,儀絕蜀道,使救不到。」
注5:據《三國志·魏志·顏斐傳》記載,後來顏斐調任平原太守時,百姓捨不得他走,「吏民啼泣遮道,車不得前,步步稽留,十餘日乃出界」。
注6:官名,亦作太子先馬(古時先與洗同音)。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中記載為太子的屬官,共設十六人,有如侍從。如淳為漢書作注說:「前驅也。《國語》曰勾踐親為夫差先馬。先或作洗也。」
注7:《三國志·蜀志·後主傳》說:「十二年春二月,亮由斜谷出,始以流馬運。」而《三國志·明帝紀》卻說:「夏四月,大疫。是月,諸葛亮出斜谷,屯渭南。」這一個多月的時間差,應該就是諸葛亮路上的時間。
注8:位於今陝西勉縣武侯鎮,該地處於褒斜道、陳倉道與祁山道的中心位置,北伐的主要三個方向都可以兼顧。
注9:當時東西方的貿易除了絲綢,還有大量胡貨。案《漢書·五行志》:「靈帝好胡服、胡帳、胡床、胡坐、胡飯、胡空侯、胡笛、胡舞,京都貴戚皆競為之。」在漢靈帝的引領下,漢末三國時期權貴圈子有一股流行胡貨的風潮,從河西走廊到成都到建業再到洛陽,胡漢貿易都非常繁盛,曹丕就曾問金城太守蘇則說:「前破酒泉、張掖,西域通使,敦煌獻徑寸大珠,可復求市益得不?」(《三國志·魏志·蘇則傳》)而當時薩珊波斯帝國滅安息,服貴霜,為絲路西線創造了相對安全和穩定的政治環境,使得絲路貿易更加繁盛,以致成都「異物崛詭,奇於八方」(左思《蜀都賦》),建業「致遠流離(琉璃)與珂珬,䌖賄紛紜,器用萬端」,洛陽則「商賈胡貊,天下四會」(《三國志·魏志·傅嘏傳》注引《傅子》),可以說都是國際貿易大都市。另外一邊,從中國到羅馬的絲綢貿易也越發繁盛,至公元四世紀羅馬史學家馬賽里努斯更在其著作《歷史》中宣稱:「過去我國僅貴族才能穿著絲服,現在則各階層人民都普遍穿用,連搬運夫和公差也不例外。」
注10:饒勝文亦指出,《魏略》為曹魏的歷史補充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,而敘述蜀漢之事,裴松之不是辯其為「妄說」,就是指其為「乖背」,其原因即在於其資料來源的局限。參閱饒勝文:《大漢帝國在巴蜀——蜀漢天命的振揚與沉墜(修訂本)》,北京聯合出版公司,2022年,第322頁。
注11:見《三國志·蜀志·後主傳》注引《魏略》:「初備在小沛,不意曹公卒至,遑遽棄家屬,後奔荊州。禪時年數歲,竄匿,隨人西入漢中,為人所賣。及建安十六年,關中破亂,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,買得禪,問知其良家子,遂養為子,與娶婦,生一子。初禪與備相失時,識其父字玄德。比舍人有姓簡者,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,備遣簡到漢中,舍都邸。禪乃詣簡,簡相檢訊,事皆符驗。簡喜,以語張魯,魯為洗沐送詣益州,備乃立以為太子。」
總之,季漢實力弱於曹魏,當以「蠶食」之策由西向東漸次推進,而不是突然鯨吞長安直至潼關。楚漢時項羽遠在彭城,故韓信閃擊三秦乃是良策,而此時曹叡近在洛陽,入援關中非常快捷。所以此一時彼一時也,魏延的「子午谷之謀」太不現實了,甚至連冒險都算不上,簡直就是送死。事實上,這個漏洞百出的計劃或許根本不存在,畢竟,魏延是劉備從基層一手提拔上來的軍事骨幹,整個給人的感覺相當務實,軍事經驗也相當豐富,而且長期駐守漢中,對周邊的地理、經濟情況了如指掌,他怎麼可能會提出這種極不靠譜的計劃呢?
如前所述,陳壽良史也,《三國志》所載原文部分基本可信,但裴松之補註的那些東西卻得打個問號,我們要好好思考一下再決定要不要採納。魏延的這個所謂「子午谷奇謀」,出自曹魏郎中魚豢私撰的史書《魏略》,《魏略》中關於曹魏的史料很有價值,畢竟魚豢是魏帝身邊之人,但季漢方面與曹魏山河阻隔,又是敵國,魚豢能有啥渠道得到季漢高層軍事會議上的信息?而且魚豢後來並未仕晉,他也得不到滅蜀之後晉所獲取的資料。所以這些恐怕只是他道聽途說來的野段子罷了(注10)。這位魚豢,似乎相當喜歡這些八卦,他還在《魏略》中記載說劉禪小時候曾被拐賣過,最後還和劉備上演了一番尋子認親的苦情戲(注11),不去做電視劇編劇真是可惜了。
注1:北方曰子,南方曰午,地理上的「子午線」也是取自這個概念。中國的建築講究中正直,所以秦始皇曾修直道溝通長安至九原長城於子午嶺,王莽則修復蝕中並改名為子午道。還有學者調查研究證實,西漢時期曾經存在一條超長距離的南北向建築基線。這條基線通過西漢都城長安中軸線延伸,向北至三原縣北塬階上一處西漢大型禮制建築遺址(並延伸至秦直道與子午嶺),南至秦嶺山麓的子午谷口(並延伸至子午道與漢中)。這條基線不僅長度超過一般建築基線,而且具有極高的直度與精確的方向性,與真子午線的夾角僅0.33度。由此可見秦漢時期在掌握長距離方位測量技術的基礎上,可能已具備了建立大面積地理坐標的能力。參閱秦建明、張在明、楊政:《陝西發現以漢長安城為中心的西漢南北向超長建築基線》,《文物》1995年第3期。
注2:其實漢中郡治一直在西城(即今陝西安康),直到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,才由從西城遷至南鄭。建安二十一年曹魏攻占漢中,分郡之東為西城郡,而以西城為其郡治,歸當地土豪魏興太守申儀管轄。
注3:詳細分析考證可見嚴耕望《唐代交通圖考》。
注4:據 《三國志·蜀志·劉封傳》注引《魏略》:「太和中,(申)儀與孟達不和,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,及達反,儀絕蜀道,使救不到。」
注5:據《三國志·魏志·顏斐傳》記載,後來顏斐調任平原太守時,百姓捨不得他走,「吏民啼泣遮道,車不得前,步步稽留,十餘日乃出界」。
注6:官名,亦作太子先馬(古時先與洗同音)。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中記載為太子的屬官,共設十六人,有如侍從。如淳為漢書作注說:「前驅也。《國語》曰勾踐親為夫差先馬。先或作洗也。」
注7:《三國志·蜀志·後主傳》說:「十二年春二月,亮由斜谷出,始以流馬運。」而《三國志·明帝紀》卻說:「夏四月,大疫。是月,諸葛亮出斜谷,屯渭南。」這一個多月的時間差,應該就是諸葛亮路上的時間。
注8:位於今陝西勉縣武侯鎮,該地處於褒斜道、陳倉道與祁山道的中心位置,北伐的主要三個方向都可以兼顧。
注9:當時東西方的貿易除了絲綢,還有大量胡貨。案《漢書·五行志》:「靈帝好胡服、胡帳、胡床、胡坐、胡飯、胡空侯、胡笛、胡舞,京都貴戚皆競為之。」在漢靈帝的引領下,漢末三國時期權貴圈子有一股流行胡貨的風潮,從河西走廊到成都到建業再到洛陽,胡漢貿易都非常繁盛,曹丕就曾問金城太守蘇則說:「前破酒泉、張掖,西域通使,敦煌獻徑寸大珠,可復求市益得不?」(《三國志·魏志·蘇則傳》)而當時薩珊波斯帝國滅安息,服貴霜,為絲路西線創造了相對安全和穩定的政治環境,使得絲路貿易更加繁盛,以致成都「異物崛詭,奇於八方」(左思《蜀都賦》),建業「致遠流離(琉璃)與珂珬,䌖賄紛紜,器用萬端」,洛陽則「商賈胡貊,天下四會」(《三國志·魏志·傅嘏傳》注引《傅子》),可以說都是國際貿易大都市。另外一邊,從中國到羅馬的絲綢貿易也越發繁盛,至公元四世紀羅馬史學家馬賽里努斯更在其著作《歷史》中宣稱:「過去我國僅貴族才能穿著絲服,現在則各階層人民都普遍穿用,連搬運夫和公差也不例外。」
注10:饒勝文亦指出,《魏略》為曹魏的歷史補充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,而敘述蜀漢之事,裴松之不是辯其為「妄說」,就是指其為「乖背」,其原因即在於其資料來源的局限。參閱饒勝文:《大漢帝國在巴蜀——蜀漢天命的振揚與沉墜(修訂本)》,北京聯合出版公司,2022年,第322頁。
注11:見《三國志·蜀志·後主傳》注引《魏略》:「初備在小沛,不意曹公卒至,遑遽棄家屬,後奔荊州。禪時年數歲,竄匿,隨人西入漢中,為人所賣。及建安十六年,關中破亂,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,買得禪,問知其良家子,遂養為子,與娶婦,生一子。初禪與備相失時,識其父字玄德。比舍人有姓簡者,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,備遣簡到漢中,舍都邸。禪乃詣簡,簡相檢訊,事皆符驗。簡喜,以語張魯,魯為洗沐送詣益州,備乃立以為太子。」
 呂純弘 • 4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