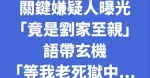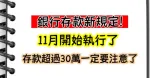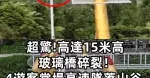2/3
下一頁
大器晚成天花板!70歲拜相104歲離世,被稱千古一相。

2/3
五羖大夫的轉折:70歲拜相
當時的秦穆公,正急於延攬賢才,百里奚的名字出現在「由余推薦」名單中,但問題來了:他身在虜中。
不在朝堂,不在戰場,而是在宋國被當奴隸使喚。
秦穆公聽說此人,有大才,但「賤而無禮,耕於野」。
按常理,一個老奴隸不配登堂,但穆公親自用「五羖皮」(五張黑山羊皮)將他贖出。
贖一個奴隸進相府,這在當時,是史無前例,贖他回來那年,他七十歲。
穆公問他:「你自比誰?」百里奚答:「姜子牙。」補一句:「我比他年輕十歲。」
姜子牙八十登台,他七十齣山,不是炫耀,而是直接回應年齡問題,他沒低頭,也沒自謙。
這個回答震住了秦國朝野,他不是求職,是赴任,穆公立即拜他為上卿,史稱「以五羖大夫治秦」。
命運饋贈的隱性優勢
他不是在七十歲那年突然開竅,是在四十年奴役中一點點積累。
虞國的滅亡給了他一個深刻認知:「亡國不因外敵,而因昏君。」
虞君貪利,重商輕政,把女兒當成外交籌碼,把大夫當作隨手可棄之人,這種「政治短視」讓百里奚牢記在心。
他形成了「以民為本」的判斷:國家的穩定,不靠強主,而靠穩民。
這是他後期推行農業改革、獎勵耕織、削弱貴族的思想底子。
在楚國養牛的十年,他把牛群當成社會,他發現,群體不是靠暴力約束,而是靠節律和適應。
牛不能疲勞放牧,人也不能日夜征戰。
他記錄草料與產奶量的對應關係,用於判斷何時放牧、何時圈養,他沒寫成表格,但秦國後期「軍農合一」制度的設計,幾乎是這套邏輯的延伸。
不是一朝覺醒,是長期觀察後的水到渠成。
治國三策:奠定秦國霸業的基石 經濟革新:鐵犁牛耕與絲綢之路雛形
他上任三年,做了兩件事。
第一:把耦犁和代田法引入關中。
當時中原的農業已逐步進入鐵器時代,而秦地仍用木犁,效率極低,百里奚從魏地、晉地引入鐵犁,配合牛耕,施行「三年耕一畝」的模式。
三年後,關中產量翻了三倍,秦國糧倉被稱「門不能閉」。
第二件事:設市舶司,開邊貿。
他觀察到秦地多鐵器,少玉石,他在西北邊界設立集市,用秦鐵換西域玉石、牛馬。
這不是單純的貿易,而是建立供應鏈,他為秦國軍隊提供戰馬,也打開了通向西域的路徑。
後世稱「絲綢之路」,初型就在這裡。
軍事改革:輕兵銳卒與西戎攻略
百里奚反對重兵團作戰,他主張精銳作戰、單兵制勝,他主張打造「輕兵銳卒」,即「兵不在多,而在精」,這不是口號,而是實戰提煉。
他挑選八百人,日夜訓練,用於突襲與游擊。《史記·秦本紀》記載:「八百銳卒,破五千魏軍。」
不僅兵制改革,他還提出「德服西戎」,不是打,而是穩,他派由余出使西戎,不帶兵、不講戰,只講農桑、教化、嫁娶。
由余是他的政治盟友,也是文化輸出者,他們通過聯姻、教育、商貿拉攏西戎部落。
十年後,秦國勢力西擴千里,邊界穩定,不戰而勝。
文化融合:中原禮樂入秦
秦地素稱「戎狄之地」,民風剽悍,缺乏禮教,百里奚設「太學」,傳授《詩》《書》,選士不問出身,只看才識。
他建立禮儀規範、移風易俗,最大改革是廢除貴族私刑,他提出「刑不過大臣」,即「貴族犯法,與民同罪」。
這一點,為後來的商鞅變法埋下思想種子,百里奚不寫法典,也不鼓勵酷刑,他主張「法之重,在公不在嚴」。
清儉本色:布衣粗食的執政者
他在秦國做了三十年上卿,封無寸土,葬時陪葬品僅一鋤一碗。
沒有玉,沒有金銀,死後下葬用舊布裹身,秦穆公欲厚葬,被婉拒,他留下的遺言是:「以牛耕始,以牛終身,不飾其身。」
他不住府邸,不用銅鏡,書房裡沒設座椅,他說『坐久血滯,志懈』。
宰相府門檻不過膝,客來無門吏阻攔,寒士亦可入堂議事。
他的書桌是石板搭木頭,案上常放殘卷,牆邊懸一隻舊水壺,壺口缺口未補。
他一生拒絕納妾,唯一妻子杜氏,自虞國亡國後始終與其漂泊四十載。
相府中,杜氏每日早起自理飲食,門人不敢呼其「夫人」,只稱「杜嫂」。
百里奚不穿錦衣、不食細糧,自稱「執政者,不可厚己。」《韓非子》評價他「可為士師,難為富貴」。
當時的秦穆公,正急於延攬賢才,百里奚的名字出現在「由余推薦」名單中,但問題來了:他身在虜中。
不在朝堂,不在戰場,而是在宋國被當奴隸使喚。
秦穆公聽說此人,有大才,但「賤而無禮,耕於野」。
按常理,一個老奴隸不配登堂,但穆公親自用「五羖皮」(五張黑山羊皮)將他贖出。
贖一個奴隸進相府,這在當時,是史無前例,贖他回來那年,他七十歲。
穆公問他:「你自比誰?」百里奚答:「姜子牙。」補一句:「我比他年輕十歲。」
姜子牙八十登台,他七十齣山,不是炫耀,而是直接回應年齡問題,他沒低頭,也沒自謙。
這個回答震住了秦國朝野,他不是求職,是赴任,穆公立即拜他為上卿,史稱「以五羖大夫治秦」。
命運饋贈的隱性優勢
他不是在七十歲那年突然開竅,是在四十年奴役中一點點積累。
虞國的滅亡給了他一個深刻認知:「亡國不因外敵,而因昏君。」
虞君貪利,重商輕政,把女兒當成外交籌碼,把大夫當作隨手可棄之人,這種「政治短視」讓百里奚牢記在心。
他形成了「以民為本」的判斷:國家的穩定,不靠強主,而靠穩民。
這是他後期推行農業改革、獎勵耕織、削弱貴族的思想底子。
在楚國養牛的十年,他把牛群當成社會,他發現,群體不是靠暴力約束,而是靠節律和適應。
牛不能疲勞放牧,人也不能日夜征戰。
他記錄草料與產奶量的對應關係,用於判斷何時放牧、何時圈養,他沒寫成表格,但秦國後期「軍農合一」制度的設計,幾乎是這套邏輯的延伸。
不是一朝覺醒,是長期觀察後的水到渠成。
治國三策:奠定秦國霸業的基石 經濟革新:鐵犁牛耕與絲綢之路雛形
他上任三年,做了兩件事。
第一:把耦犁和代田法引入關中。
當時中原的農業已逐步進入鐵器時代,而秦地仍用木犁,效率極低,百里奚從魏地、晉地引入鐵犁,配合牛耕,施行「三年耕一畝」的模式。
三年後,關中產量翻了三倍,秦國糧倉被稱「門不能閉」。
第二件事:設市舶司,開邊貿。
他觀察到秦地多鐵器,少玉石,他在西北邊界設立集市,用秦鐵換西域玉石、牛馬。
這不是單純的貿易,而是建立供應鏈,他為秦國軍隊提供戰馬,也打開了通向西域的路徑。
後世稱「絲綢之路」,初型就在這裡。
軍事改革:輕兵銳卒與西戎攻略
百里奚反對重兵團作戰,他主張精銳作戰、單兵制勝,他主張打造「輕兵銳卒」,即「兵不在多,而在精」,這不是口號,而是實戰提煉。
他挑選八百人,日夜訓練,用於突襲與游擊。《史記·秦本紀》記載:「八百銳卒,破五千魏軍。」
不僅兵制改革,他還提出「德服西戎」,不是打,而是穩,他派由余出使西戎,不帶兵、不講戰,只講農桑、教化、嫁娶。
由余是他的政治盟友,也是文化輸出者,他們通過聯姻、教育、商貿拉攏西戎部落。
十年後,秦國勢力西擴千里,邊界穩定,不戰而勝。
文化融合:中原禮樂入秦
秦地素稱「戎狄之地」,民風剽悍,缺乏禮教,百里奚設「太學」,傳授《詩》《書》,選士不問出身,只看才識。
他建立禮儀規範、移風易俗,最大改革是廢除貴族私刑,他提出「刑不過大臣」,即「貴族犯法,與民同罪」。
這一點,為後來的商鞅變法埋下思想種子,百里奚不寫法典,也不鼓勵酷刑,他主張「法之重,在公不在嚴」。
清儉本色:布衣粗食的執政者
他在秦國做了三十年上卿,封無寸土,葬時陪葬品僅一鋤一碗。
沒有玉,沒有金銀,死後下葬用舊布裹身,秦穆公欲厚葬,被婉拒,他留下的遺言是:「以牛耕始,以牛終身,不飾其身。」
他不住府邸,不用銅鏡,書房裡沒設座椅,他說『坐久血滯,志懈』。
宰相府門檻不過膝,客來無門吏阻攔,寒士亦可入堂議事。
他的書桌是石板搭木頭,案上常放殘卷,牆邊懸一隻舊水壺,壺口缺口未補。
他一生拒絕納妾,唯一妻子杜氏,自虞國亡國後始終與其漂泊四十載。
相府中,杜氏每日早起自理飲食,門人不敢呼其「夫人」,只稱「杜嫂」。
百里奚不穿錦衣、不食細糧,自稱「執政者,不可厚己。」《韓非子》評價他「可為士師,難為富貴」。
 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