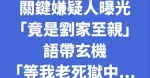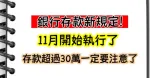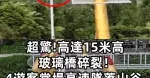4/4
下一頁
他死於1641年,他的行為卻傳到了2025年

4/4
▲《典籍里的中國》中的徐霞客形象。圖源:典籍里的中國
在徐霞客30餘年的旅遊經歷中,西南之游是最為艱苦卓絕的一次。他為這次出遊謀劃了很多年,一直擔心再不出發就年老力衰去不了了。
1636年10月,終於打點行裝出發,他已經50歲。
此行,他只攜帶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,除了暖身的衣服和盤纏外,沒有準備任何防身的武器。他的遠遊冠中,藏著母親生前給他的禮物——一把銀簪。母親在他首次旅行時,將此銀簪縫於帽中,以備不測之用。
他隨身的考察工具極為簡樸,一支筆,一個指南針,卻肩負著豐富的書籍,都是一些派得上用場的地理資料。
最後,他不得不懷揣朋友們的引薦信,以便在危難的時候向地方官求助,或籌措路費。
和他一同出發的,有兩個人。一個是僕人兼導遊顧仆,另一個是和尚靜聞。
靜聞是要到雲南雞足山朝聖的。顧仆可能背著一把鏟子,用徐霞客的話說,隨時隨地可以埋葬他的身軀。
徐霞客在啟程之前已作好遇難捐軀的思想準備。在寫給大名士陳繼儒的信里,他說,萬一有個三長兩短,死在這片「絕域」,做一個「遊魂」我也願意。
旅程的艱險,確實「對得起」他的思想準備:三次遭遇強盜,四次絕糧。
一路下來,他練就了貝爺一般的荒野求生能力,可以幾天不吃飯,都沒問題。
在湘江的船上,一夥強盜趁著月色來打劫。徐霞客跳江逃生,喪失了隨身的財物,僅剩一褲一襪。靜聞為了保護血寫的經書,死守船中,身負重傷。顧仆也受了傷。
儘管備受打擊,徐霞客沒有考慮返程。他的方向不會變。
最終,靜聞死在路上。徐霞客帶著他的骨灰和經書,直奔雞足山,完成了這名風雨同路人的遺願。
在雲南保山漫遊時,有人要到江蘇,問徐霞客要不要幫他帶家書回去。
徐霞客猶豫許久,婉言謝絕了。他說:「浮沉之身,恐家人已認為無定河邊物;若書至家中,知身猶在,又恐身反不在也……」
不過,當晚,他為此失眠了,還是寫了一封家書。
對他來說,死亡是每天可能邂逅的東西。所以,是死是生,都是兩可,無從預知自己能否看到明天的太陽。
1640年,這次萬里遠遊以一場致命的疾病結束。
徐霞客感染了足疾,雙腳盡廢。一幫人用滑竿,把他抬回了江陰。
1641年,徐霞客溘然長逝。
徐霞客在世的時候,他的朋友圈已經公認他是奇人怪咖。
曾任宰輔的文震孟說:「霞客生平無他事,無他嗜,日遑遑遊行天下名山。自五嶽之外,若匡廬、羅浮、峨眉、嵾嶺,足跡殆遍。真古今第一奇人也。」
當時的文壇領袖錢謙益也說,徐霞客是千古奇人,《徐霞客遊記》是千古奇書。
晚明旅遊之風那麼盛,登山不怕死的也不少,為什麼只有徐霞客游成了「奇人」?
最根本的原因是,徐霞客跟其他任何一個旅遊者,都不一樣!
他是一個「三無人員」:無編制,無職業,無功利心。
袁宏道經常在遊記里把自己描寫成離經叛道的怪傑,但他與徐霞客的距離,至少差了一個王士性。
這三人,都是晚明最著名的旅遊達人,但除了晚輩徐霞客,其他兩人都有編制。他們的旅遊,在當時被稱為「宦遊」,就是借著外地做官或公務考察之機,順便旅遊。
徐霞客不一樣。他是個字面意義上的「無業游民」,為了旅遊而旅遊。或者說,他的職業就是旅遊,他的人生就是旅遊,為旅遊而活,活著為了旅遊。
這樣的職業旅行家,在傳統中國社會是獨一無二的。
所以,他比其他任何旅遊者走得更遠,也更專業,更賣命。
清朝文人潘耒評價他,說「以性靈游,以軀命游,亘古以來一人而已」。
他途窮不憂,行誤不悔,多次遇盜,幾度絕糧,但仍孜孜不倦去探索大自然的未知領域,瞑則寢樹石之間,飢則啖草木之實,不避風雨,不憚虎狼。
他擺脫了視遊山玩水為陶冶情操之道的傳統模式,賦予了旅遊更具科學探索與冒險精神的內涵。
他征服過的地方,往往是漁人樵夫都很少抵達的荒郊,或是猿猴飛鳥深藏其中的山壑。
他白天旅行探險,晚上伏燈寫作,有時甚至就著破壁枯樹,「燃松拾穗,走筆為記」。
他以客觀嚴謹的態度,每天忠實記錄下當天的行走路線,沿途所見的山川風貌與風土人情,以及他的心得體會。
他寫遊記,壓根兒不是為了發表。早期是寫給母親看,讓母親可以「臥游」,對兒子走過的名山大川如身臨其境。後來,寫著寫著,寫成了習慣,或許就把寫日記當成了自己與自己的對話而已。
他生前並未發表任何遊記。死後他的朋友替他整理日記文稿,但很多內容已經散佚了。
他所做的一切,純粹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求知慾和好奇心。除此之外,他沒有什麼功利心,也沒想什麼實用價值。
也正因此,他才不會變得短視,而使得自己的人生與文字在幾個世紀之後仍然散發著理性的光輝。
相比之下,那些斤斤計較於當下的人和事,早已淪為歷史的塵埃。
很多人喜歡拿徐霞客和陶淵明做比較,因為他們都絕跡官場、不計功名、鍾情山水。
但我認為,徐霞客跟陶淵明也完全不一樣。
徐霞客的經歷與選擇,實際上突破了傳統的隱居守節處世模式,標誌著一種新人生觀的養成。
他開闢了另一種人生行走的模式,將超脫世俗的路子指向了務實求真的具有科學曙光的方向,避免自己成為陶淵明的複製品。
而陶淵明的隱居,是先秦歷史典故中早就建構起來的傳統。陶並沒有任何獨創性在裡面。
面對徐霞客這樣的怪咖,我們幾乎無法作出合乎社會規範的評價。不管是晚明的規範,還是現在的規範,似乎都容納不了這樣一個人。
我們現在把徐霞客捧得那麼高,無非看中了人家遊記中體現的科學精神。
但這個東西,徐霞客本人並不在乎。他的遊記流傳下來,本身就帶有偶然性。
如果他的遊記失傳了,我們還會把他捧得這麼高嗎?
我想,肯定不會。
我們會說他不求上進啦,荒廢時光啦,社會寄生蟲啦……總之,有一百零一個理由來否定他。
清代紀曉嵐評價徐霞客時,顯然遇到了類似困境。他在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給予《徐霞客遊記》較高的評價,說「其書為山經之別乘,輿記之外篇,可補充地理之學」。
但他對徐霞客的人生選擇並不讚賞,所以對徐霞客的旅遊動機進行了揣測和批評,說徐霞客「耽奇嗜僻,刻意遠遊」。
這八個字什麼意思?
就是說,徐霞客性情怪僻,慣於標新立異,處心積慮地遊走他方並沉溺於其中,有沽名釣譽之嫌。
這種調調,很像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的普遍心理:你的行為超出了我的想像,所以是可疑的。
我們質疑有錢人的慷慨,你為什麼捐這麼多錢,不就是圖個名聲嗎?我們質疑沒錢人的苦難,你為什麼表演貧窮,不就是想獲取愛心款嗎?……
我們質疑一切。質疑到最後,無非就是被標準答案限制了想像力。
在一個功利的社會,做什麼事,都要追尋一下意義。而意義的定義權,牢牢把控在集體手裡。
徐霞客覺得他的活法很有意義。對不起,我們集體覺得你沒意義,你就沒意義。
但,總有一些超越世俗的無意義的事情,總有一種純粹的內心需求,孤懸著,沒人理解。
人生的標準化,是從標準答案開始的。你應該活成什麼樣子,什麼時候應該幹什麼事,這些都被認為有標準答案。每個人都要對照標準答案作答。
徐霞客跑題了,故而只能被歸入「千古奇人」。這可能是讚賞,但更多表達的是不認同:你跟我們不是一類人。
殊不知:沒有意義,有時正是人生最大的意義。
致敬,不為意義而活的徐霞客!
在徐霞客30餘年的旅遊經歷中,西南之游是最為艱苦卓絕的一次。他為這次出遊謀劃了很多年,一直擔心再不出發就年老力衰去不了了。
1636年10月,終於打點行裝出發,他已經50歲。
此行,他只攜帶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,除了暖身的衣服和盤纏外,沒有準備任何防身的武器。他的遠遊冠中,藏著母親生前給他的禮物——一把銀簪。母親在他首次旅行時,將此銀簪縫於帽中,以備不測之用。
他隨身的考察工具極為簡樸,一支筆,一個指南針,卻肩負著豐富的書籍,都是一些派得上用場的地理資料。
最後,他不得不懷揣朋友們的引薦信,以便在危難的時候向地方官求助,或籌措路費。
和他一同出發的,有兩個人。一個是僕人兼導遊顧仆,另一個是和尚靜聞。
靜聞是要到雲南雞足山朝聖的。顧仆可能背著一把鏟子,用徐霞客的話說,隨時隨地可以埋葬他的身軀。
徐霞客在啟程之前已作好遇難捐軀的思想準備。在寫給大名士陳繼儒的信里,他說,萬一有個三長兩短,死在這片「絕域」,做一個「遊魂」我也願意。
旅程的艱險,確實「對得起」他的思想準備:三次遭遇強盜,四次絕糧。
一路下來,他練就了貝爺一般的荒野求生能力,可以幾天不吃飯,都沒問題。
在湘江的船上,一夥強盜趁著月色來打劫。徐霞客跳江逃生,喪失了隨身的財物,僅剩一褲一襪。靜聞為了保護血寫的經書,死守船中,身負重傷。顧仆也受了傷。
儘管備受打擊,徐霞客沒有考慮返程。他的方向不會變。
最終,靜聞死在路上。徐霞客帶著他的骨灰和經書,直奔雞足山,完成了這名風雨同路人的遺願。
在雲南保山漫遊時,有人要到江蘇,問徐霞客要不要幫他帶家書回去。
徐霞客猶豫許久,婉言謝絕了。他說:「浮沉之身,恐家人已認為無定河邊物;若書至家中,知身猶在,又恐身反不在也……」
不過,當晚,他為此失眠了,還是寫了一封家書。
對他來說,死亡是每天可能邂逅的東西。所以,是死是生,都是兩可,無從預知自己能否看到明天的太陽。
1640年,這次萬里遠遊以一場致命的疾病結束。
徐霞客感染了足疾,雙腳盡廢。一幫人用滑竿,把他抬回了江陰。
1641年,徐霞客溘然長逝。
徐霞客在世的時候,他的朋友圈已經公認他是奇人怪咖。
曾任宰輔的文震孟說:「霞客生平無他事,無他嗜,日遑遑遊行天下名山。自五嶽之外,若匡廬、羅浮、峨眉、嵾嶺,足跡殆遍。真古今第一奇人也。」
當時的文壇領袖錢謙益也說,徐霞客是千古奇人,《徐霞客遊記》是千古奇書。
晚明旅遊之風那麼盛,登山不怕死的也不少,為什麼只有徐霞客游成了「奇人」?
最根本的原因是,徐霞客跟其他任何一個旅遊者,都不一樣!
他是一個「三無人員」:無編制,無職業,無功利心。
袁宏道經常在遊記里把自己描寫成離經叛道的怪傑,但他與徐霞客的距離,至少差了一個王士性。
這三人,都是晚明最著名的旅遊達人,但除了晚輩徐霞客,其他兩人都有編制。他們的旅遊,在當時被稱為「宦遊」,就是借著外地做官或公務考察之機,順便旅遊。
徐霞客不一樣。他是個字面意義上的「無業游民」,為了旅遊而旅遊。或者說,他的職業就是旅遊,他的人生就是旅遊,為旅遊而活,活著為了旅遊。
這樣的職業旅行家,在傳統中國社會是獨一無二的。
所以,他比其他任何旅遊者走得更遠,也更專業,更賣命。
清朝文人潘耒評價他,說「以性靈游,以軀命游,亘古以來一人而已」。
他途窮不憂,行誤不悔,多次遇盜,幾度絕糧,但仍孜孜不倦去探索大自然的未知領域,瞑則寢樹石之間,飢則啖草木之實,不避風雨,不憚虎狼。
他擺脫了視遊山玩水為陶冶情操之道的傳統模式,賦予了旅遊更具科學探索與冒險精神的內涵。
他征服過的地方,往往是漁人樵夫都很少抵達的荒郊,或是猿猴飛鳥深藏其中的山壑。
他白天旅行探險,晚上伏燈寫作,有時甚至就著破壁枯樹,「燃松拾穗,走筆為記」。
他以客觀嚴謹的態度,每天忠實記錄下當天的行走路線,沿途所見的山川風貌與風土人情,以及他的心得體會。
他寫遊記,壓根兒不是為了發表。早期是寫給母親看,讓母親可以「臥游」,對兒子走過的名山大川如身臨其境。後來,寫著寫著,寫成了習慣,或許就把寫日記當成了自己與自己的對話而已。
他生前並未發表任何遊記。死後他的朋友替他整理日記文稿,但很多內容已經散佚了。
他所做的一切,純粹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求知慾和好奇心。除此之外,他沒有什麼功利心,也沒想什麼實用價值。
也正因此,他才不會變得短視,而使得自己的人生與文字在幾個世紀之後仍然散發著理性的光輝。
相比之下,那些斤斤計較於當下的人和事,早已淪為歷史的塵埃。
很多人喜歡拿徐霞客和陶淵明做比較,因為他們都絕跡官場、不計功名、鍾情山水。
但我認為,徐霞客跟陶淵明也完全不一樣。
徐霞客的經歷與選擇,實際上突破了傳統的隱居守節處世模式,標誌著一種新人生觀的養成。
他開闢了另一種人生行走的模式,將超脫世俗的路子指向了務實求真的具有科學曙光的方向,避免自己成為陶淵明的複製品。
而陶淵明的隱居,是先秦歷史典故中早就建構起來的傳統。陶並沒有任何獨創性在裡面。
面對徐霞客這樣的怪咖,我們幾乎無法作出合乎社會規範的評價。不管是晚明的規範,還是現在的規範,似乎都容納不了這樣一個人。
我們現在把徐霞客捧得那麼高,無非看中了人家遊記中體現的科學精神。
但這個東西,徐霞客本人並不在乎。他的遊記流傳下來,本身就帶有偶然性。
如果他的遊記失傳了,我們還會把他捧得這麼高嗎?
我想,肯定不會。
我們會說他不求上進啦,荒廢時光啦,社會寄生蟲啦……總之,有一百零一個理由來否定他。
清代紀曉嵐評價徐霞客時,顯然遇到了類似困境。他在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給予《徐霞客遊記》較高的評價,說「其書為山經之別乘,輿記之外篇,可補充地理之學」。
但他對徐霞客的人生選擇並不讚賞,所以對徐霞客的旅遊動機進行了揣測和批評,說徐霞客「耽奇嗜僻,刻意遠遊」。
這八個字什麼意思?
就是說,徐霞客性情怪僻,慣於標新立異,處心積慮地遊走他方並沉溺於其中,有沽名釣譽之嫌。
這種調調,很像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的普遍心理:你的行為超出了我的想像,所以是可疑的。
我們質疑有錢人的慷慨,你為什麼捐這麼多錢,不就是圖個名聲嗎?我們質疑沒錢人的苦難,你為什麼表演貧窮,不就是想獲取愛心款嗎?……
我們質疑一切。質疑到最後,無非就是被標準答案限制了想像力。
在一個功利的社會,做什麼事,都要追尋一下意義。而意義的定義權,牢牢把控在集體手裡。
徐霞客覺得他的活法很有意義。對不起,我們集體覺得你沒意義,你就沒意義。
但,總有一些超越世俗的無意義的事情,總有一種純粹的內心需求,孤懸著,沒人理解。
人生的標準化,是從標準答案開始的。你應該活成什麼樣子,什麼時候應該幹什麼事,這些都被認為有標準答案。每個人都要對照標準答案作答。
徐霞客跑題了,故而只能被歸入「千古奇人」。這可能是讚賞,但更多表達的是不認同:你跟我們不是一類人。
殊不知:沒有意義,有時正是人生最大的意義。
致敬,不為意義而活的徐霞客!
 呂純弘 • 4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