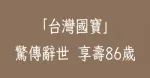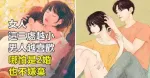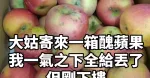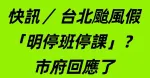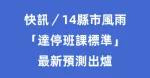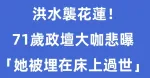2/2
下一頁
杜月笙晚年落寞去借錢,此人一句話沒問就說:要多少杜先生自己填

2/2
但杜月笙不是輕易服輸的人,他依然是上海灘的「大當家」,黑白兩道通吃,地頭蛇就是再沒官職,也有千軍萬馬。
於是,他將眼光放在另一場政治較量上,市參議會議長的選舉。
這場選舉,民國政府打著「民主」旗號對外宣稱「公正公開」,實則各方勢力暗流洶湧。
杜月笙深諳此道,在選舉前夕頻頻出現在酒樓飯莊,與各路「代言人」密會,一方面許以厚利,另一方面放出風聲「誰不支持杜先生,將來日子恐難安生」。
他的影響力之大,使得不少選票主動向他靠攏。
最終公布的結果毫無懸念,杜月笙高票當選為市參議會議長。
只是這場得意,轉瞬即逝。
不久,一記悶雷炸響,杜月笙的心腹萬墨林被警備司令宣鐵吾突襲拘捕,罪名是「囤積居奇」。
消息一出,黑白兩道為之震動,杜月笙立刻明白,這不是清理黑市,而是有組織、有目標的打擊行動。
緊接著更重的一錘砸下,蔣介石通過密信傳達:「議長一職,由潘公展擔任更妥。」
這幾乎是明牌打臉,逼杜月笙下台,杜月笙雖惱怒,卻知形勢已非他可掌控。
幾經猶豫,他終於宣布辭去議長之職,避而不談退讓原因。
此後,街頭風聲驟變,「打倒三大流氓」的標語如雨後春筍般出現。
那些曾對杜月笙畢恭畢敬的手下也悄然收斂行跡,昔日掌控上海半壁江山的「皇帝」,如今連一個議長位置都坐不穩。
眼見局勢每況愈下,杜月笙不得不做出抉擇。
政治不是江湖,利益面前,誰都是棄子。
流亡香港江湖散
1949年,帶著一腔鬱鬱不平,杜月笙舉家離開了上海,不再有往昔的意氣風發。
到了香港,杜月笙起初仍保留著昔日大佬的派頭。
他在港島租下豪宅,每日賓客盈門,車水馬龍,談笑風生,可惜,風光背後早埋下了衰落的種子。
在上海時,他以「三鑫公司」控制法租界鴉片轉運,又通過「中匯銀行」掌控金融命脈,錢財如潮水般湧入。
可到了香港,失去後台和地緣優勢,他便如離水之魚,難以適應。
再者,一大家子三十餘口的吃喝用度,延續著上海的奢靡舊風,從餐桌上的鮑參翅肚,到女眷衣箱中每日更換的旗袍首飾,再到定期召開的「敘舊宴席」,杜府的開銷每日如流水般消失。
他或許始終相信,江湖講究一個「情」字。
昔日自己仗義疏財,救人無數,如今稍有拮据,向老朋友借點周轉資金,當不在話下。
於是他先後託人發信、登門、致電,請求舊日門生、政要、商賈相助,他以為只要開口,對方自然會報恩,但現實如冰水當頭。
昔日一聲「杜先生」喊得山響的熟人,接到信件多以「尚在商議」、「暫無餘資」推脫,有人甚至連面都不見,轉由門房回話,說「東主近日出國」,語氣冷淡。
彼時的香港,正是舊勢力洗牌、新秩序初建的年代。
大陸來港的政客、富商、學者比比皆是,而杜月笙雖有名氣,但早已沒有了實權地盤。
他的「青幫背景」在此地不值一提,港英政府對其存疑,香港黑幫則各自為王,根本不買他的帳。
他以前或許存的是交情,可惜,現在這世道,情義這東西也得看市價。
為了支撐日常開銷,他被迫陸續變賣在上海留下的幾處房產與地皮。
可這不過是是「飲鴆止渴」,錢總有花完的一天,果然,這些資產所換來的資本被迅速消耗,所剩無幾。
那段日子,杜府的景象漸漸冷清,連管家也開始精打細算。
那一年,杜月笙六十有餘,身邊只剩下寥寥幾個舊仆和妻小。
他沒有徹底跌入貧窮,但已無力維持曾經的高光生活,他親歷了江湖散盡、人情冷暖,他失去了金錢、失去了地位,也失去了信心。
可也正是在這種絕境中,他再次想起了一個名字,劉航琛。
正是那份早年結下的恩義,成為他命運轉折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一紙支票顯人性恩仇
選定日子,杜月笙一身素凈長袍,坐上老舊的黑車駛向劉府。
到達門前,僕人認出他,趕忙通傳,不一會兒,劉航琛親自迎了出來,神色清朗,步伐穩健。
二人對坐,寒暄未幾,杜月笙開門見山:「今日來此,是為借款。」
他眼神坦然,語氣中帶著一絲尷尬,但沒有卑微。
劉航琛聞言未作多言,從抽屜中取出一張空白支票,輕輕放在茶几上,語氣平穩卻鄭重地說:
「杜先生,150萬以下,隨便填,若是更多,事先告訴我一聲就行。」
杜月笙一時間未語,這種毫無條件、毫無顧慮的信任,早已不多見。
他沒有濫用這份信任,只取所需,足以維持數月家中生計,劉航琛沒有問他借款的去處,也不在乎他何時歸還。
1951年,杜月笙病逝於香港。
他去世前燒毀了所有別人寫給他的欠條,還告誡子孫,不要追回欠債。
於是,他將眼光放在另一場政治較量上,市參議會議長的選舉。
這場選舉,民國政府打著「民主」旗號對外宣稱「公正公開」,實則各方勢力暗流洶湧。
杜月笙深諳此道,在選舉前夕頻頻出現在酒樓飯莊,與各路「代言人」密會,一方面許以厚利,另一方面放出風聲「誰不支持杜先生,將來日子恐難安生」。
他的影響力之大,使得不少選票主動向他靠攏。
最終公布的結果毫無懸念,杜月笙高票當選為市參議會議長。
只是這場得意,轉瞬即逝。
不久,一記悶雷炸響,杜月笙的心腹萬墨林被警備司令宣鐵吾突襲拘捕,罪名是「囤積居奇」。
消息一出,黑白兩道為之震動,杜月笙立刻明白,這不是清理黑市,而是有組織、有目標的打擊行動。
緊接著更重的一錘砸下,蔣介石通過密信傳達:「議長一職,由潘公展擔任更妥。」
這幾乎是明牌打臉,逼杜月笙下台,杜月笙雖惱怒,卻知形勢已非他可掌控。
幾經猶豫,他終於宣布辭去議長之職,避而不談退讓原因。
此後,街頭風聲驟變,「打倒三大流氓」的標語如雨後春筍般出現。
那些曾對杜月笙畢恭畢敬的手下也悄然收斂行跡,昔日掌控上海半壁江山的「皇帝」,如今連一個議長位置都坐不穩。
眼見局勢每況愈下,杜月笙不得不做出抉擇。
政治不是江湖,利益面前,誰都是棄子。
流亡香港江湖散
1949年,帶著一腔鬱鬱不平,杜月笙舉家離開了上海,不再有往昔的意氣風發。
到了香港,杜月笙起初仍保留著昔日大佬的派頭。
他在港島租下豪宅,每日賓客盈門,車水馬龍,談笑風生,可惜,風光背後早埋下了衰落的種子。
在上海時,他以「三鑫公司」控制法租界鴉片轉運,又通過「中匯銀行」掌控金融命脈,錢財如潮水般湧入。
可到了香港,失去後台和地緣優勢,他便如離水之魚,難以適應。
再者,一大家子三十餘口的吃喝用度,延續著上海的奢靡舊風,從餐桌上的鮑參翅肚,到女眷衣箱中每日更換的旗袍首飾,再到定期召開的「敘舊宴席」,杜府的開銷每日如流水般消失。
他或許始終相信,江湖講究一個「情」字。
昔日自己仗義疏財,救人無數,如今稍有拮据,向老朋友借點周轉資金,當不在話下。
於是他先後託人發信、登門、致電,請求舊日門生、政要、商賈相助,他以為只要開口,對方自然會報恩,但現實如冰水當頭。
昔日一聲「杜先生」喊得山響的熟人,接到信件多以「尚在商議」、「暫無餘資」推脫,有人甚至連面都不見,轉由門房回話,說「東主近日出國」,語氣冷淡。
彼時的香港,正是舊勢力洗牌、新秩序初建的年代。
大陸來港的政客、富商、學者比比皆是,而杜月笙雖有名氣,但早已沒有了實權地盤。
他的「青幫背景」在此地不值一提,港英政府對其存疑,香港黑幫則各自為王,根本不買他的帳。
他以前或許存的是交情,可惜,現在這世道,情義這東西也得看市價。
為了支撐日常開銷,他被迫陸續變賣在上海留下的幾處房產與地皮。
可這不過是是「飲鴆止渴」,錢總有花完的一天,果然,這些資產所換來的資本被迅速消耗,所剩無幾。
那段日子,杜府的景象漸漸冷清,連管家也開始精打細算。
那一年,杜月笙六十有餘,身邊只剩下寥寥幾個舊仆和妻小。
他沒有徹底跌入貧窮,但已無力維持曾經的高光生活,他親歷了江湖散盡、人情冷暖,他失去了金錢、失去了地位,也失去了信心。
可也正是在這種絕境中,他再次想起了一個名字,劉航琛。
正是那份早年結下的恩義,成為他命運轉折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一紙支票顯人性恩仇
選定日子,杜月笙一身素凈長袍,坐上老舊的黑車駛向劉府。
到達門前,僕人認出他,趕忙通傳,不一會兒,劉航琛親自迎了出來,神色清朗,步伐穩健。
二人對坐,寒暄未幾,杜月笙開門見山:「今日來此,是為借款。」
他眼神坦然,語氣中帶著一絲尷尬,但沒有卑微。
劉航琛聞言未作多言,從抽屜中取出一張空白支票,輕輕放在茶几上,語氣平穩卻鄭重地說:
「杜先生,150萬以下,隨便填,若是更多,事先告訴我一聲就行。」
杜月笙一時間未語,這種毫無條件、毫無顧慮的信任,早已不多見。
他沒有濫用這份信任,只取所需,足以維持數月家中生計,劉航琛沒有問他借款的去處,也不在乎他何時歸還。
1951年,杜月笙病逝於香港。
他去世前燒毀了所有別人寫給他的欠條,還告誡子孫,不要追回欠債。
 呂純弘 • 11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
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
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