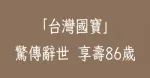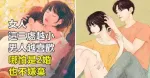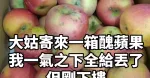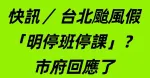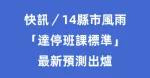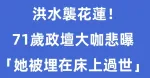1/3
下一頁
世人皆知「聞雞起舞」,卻不知祖逖的最終下場,許多老師都不願講

1/3
世人皆知「聞雞起舞」,卻不知祖逖的最終下場,許多老師都不願講
「聞雞起舞」這個勵志故事想必大家都聽過。
祖逖和劉琨,兩位少年英雄,半夜聞雞鳴即起身練劍,立志報國。
他們的勤奮被傳頌千年,成為激勵後人的典範。
可歷史的真相往往殘酷,老師不會告訴你,這兩位英雄的結局,或許淒涼的讓人難以想像。
他們經歷了什麼?又為何會有慘痛下場?
少年壯志、亂世伏筆
洛陽司州主簿的官署內,祖逖和劉琨這對摯友,又一次抵足而談,直至深夜。
他們的話題從詩書禮樂到天下大勢,從朝堂詭譎到邊疆烽火,言語間儘是少年人的熱血抱負。
他們並不知道,多年後,這段在洛陽的歲月會成為「聞雞起舞」的傳奇,而他們的命運,也將隨著這個搖搖欲墜的王朝一同沉浮。
那時的西晉,表面仍維持著大一統的繁華,內里卻早已危機四伏。
晉惠帝司馬衷痴愚無能,朝政被皇后賈南風一手操控,而各地藩王虎視眈眈,暗流涌動。
更可怕的是,北方胡人部落趁著朝廷內鬥,不斷南下侵擾,邊境烽煙四起。
祖逖出身范陽豪族,自幼不拘小節,輕財重義,常散盡家財接濟貧苦鄉鄰。
他的身上既有豪俠的慷慨,又有士人的抱負。
劉琨則來自中山劉氏,風姿俊朗,文采斐然,二十歲時便以文章名動洛陽,被譽為「洛中奕奕,慶孫越石」。
兩人性格迥異,卻因共同的志向成為莫逆之交。
他們不甘心只做案牘勞形的小吏,而是渴望在亂世中力挽狂瀾,哪怕前路荊棘密布。
某個凌晨,天尚未亮,一聲雞鳴劃破寂靜。
祖逖猛然驚醒,推醒身旁的劉琨。
劉琨睡眼惺忪,喃喃道:「此時雞鳴,恐非吉兆。」
祖逖卻目光炯炯,朗聲道:「此非惡聲也!天下將亂,正是男兒奮發之時,豈能虛度光陰?」
說罷,他翻身下榻,拔劍出鞘,在月光下揮灑起來。
劉琨見狀,胸中豪氣頓生,亦提劍相隨。
這一刻,雞鳴不再只是尋常的晨號,而成了他們生命中一道無形的戰鼓,催促著他們向未知的命運進發。
但現實遠比理想殘酷,洛陽的朝堂上,賈南風專權跋扈,誅殺太子,引發諸王不滿。
邊疆的胡人部落蠢蠢欲動,而朝廷卻無暇顧及。
江統曾上書《徙戎論》,警告朝廷若不驅逐內遷胡人,必成大患,可他的諫言如石沉大海。
大廈將傾,獨木難支,祖逖與劉琨的滿腔熱血,在時代的洪流面前,顯得如此渺小。
他們仍在等待機會。
歷史從不缺少英雄,但英雄的結局,往往由時代書寫。
不管未來怎樣,但此刻,他們只是兩個心懷壯志的年輕人,在雞鳴聲中,迎向屬於自己的黎明。
八王之亂
起初,祖逖對齊王司馬冏寄予厚望。
這位年輕的藩王素有賢名,入主洛陽後廣納賢才,似乎真有重振朝綱的魄力。
祖逖被徵召為大司馬掾,每日埋首案牘,起草文書,試圖在混亂中維持一絲秩序。
可好景不長,司馬冏很快沉溺權欲,驕縱跋扈,最終被長沙王司馬乂所殺。
理想尚未展開,便已破滅,祖逖第一次嘗到了政治幻滅的苦澀。
與此同時,劉琨的處境同樣艱難。
他輾轉於諸王之間,憑藉過人的才略漸露頭角,可每一次站隊都如同刀尖行走。
八王混戰,今日的盟友可能就是明日的仇敵,忠誠成了最廉價的籌碼。
在這片權力的焦土上,道德和理想被碾得粉碎,活下來的法則只剩下審時度勢與冷酷算計。
最令祖逖心寒的,是東海王司馬越的崛起。
這位權臣打著匡扶晉室的旗號,卻將晉惠帝當作傀儡,肆意弄權。
祖逖曾短暫效力於他,可很快就發現,所謂的"忠君"不過是司馬越野心的遮羞布。
當司馬越將皇帝劫持至長安,自己獨攬朝政時,祖逖徹底失望了。
他原以為能在這亂世中尋得明主,可兜兜轉轉,發現自己效忠的不過是一群精緻的利己主義者。
北方的戰火越燒越旺。
匈奴人劉淵在并州自立為王,羯族首領石勒縱橫河北,而朝廷的精銳卻在諸王的內鬥中消耗殆盡。
劉琨被派往并州任刺史,名義上是鎮守邊疆,實則是被丟進了一片死地。
當他帶著千餘殘兵抵達晉陽時,眼前的景象令人絕望,城牆殘破,屍骸遍野,胡騎在城外游弋,而朝廷的援軍遙遙無期。
這是一座被遺忘的孤城,也是一塊試煉英雄的磨刀石。
令人驚嘆的是,劉琨硬是在這片廢墟上創造了奇蹟。
他安撫流民,重建城防,甚至用胡笳聲勾起匈奴士兵的鄉愁,瓦解敵軍的鬥志。
短短一年間,晉陽竟重現生機,成為北方抗胡的重要據點。
可就在形勢稍有好轉時,內部的傾軋又給了劉琨致命一擊。
他信任的部下相互攻訐,鮮卑盟友反覆無常,而遠在建康的朝廷除了空頭封賞,給不了任何實質支持。
個人的才能終究敵不過體制的腐朽,英雄的孤獨,在這一刻顯得格外刺目。
當劉琨在晉陽苦苦支撐時,祖逖選擇了另一條路。
母親去世後,他借守孝之名遠離朝堂,冷眼旁觀這場權力的狂歡。
311年,洛陽陷落,匈奴人縱兵屠城的消息傳來,他終於下定決心,帶著數百族人南渡淮河,投奔琅琊王司馬睿。
這是逃避,也是新的開始,在南方的煙雨樓台中,一個更宏大的計劃正在他心中醞釀。
亂世中的選擇,往往無關對錯,只關乎生存信念。
祖逖南下,劉琨北上,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,卻同樣荊棘叢生。
英雄的絕唱
建康城司馬睿的王府內,祖逖站在殿中,言辭懇切,目光如炬。
他剛剛向這位琅琊王陳述了北伐的計劃,描繪著收復中原的藍圖。
司馬睿微微頷首,臉上掛著禮節性的讚許,可眼神卻飄向了窗外。
祖逖沒有說破,但他心裡清楚,這位未來的東晉開國之君,關心的從來不是北方的遺民,而是江南的安穩。
朝廷的"支持"寒酸得令人心酸,一千人的糧餉,三千匹布帛,沒有一兵一卒。
但祖逖接下了這道幾乎等於放逐的任命。
313年秋,他帶著百餘親族部曲在京口渡江。
船至中流,江風獵獵,祖逖突然起身,以槳擊水,朗聲道:
"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,有如大江!"
這誓言如金石墜地,在歷史的迴音壁上震盪千年,可當時在場的部曲們,只聽見了風中隱約的嘆息。
北伐的開端比想像中艱難,中原歷經戰亂,早已是塢堡林立,豪強割據的局面。
祖逖的使者殷乂因出言不遜被張平所殺,第一次交鋒就見了血。
在中原的廢墟上,沒有王師的榮耀,只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。
轉折發生在一次夜襲。樊雅率死士突襲祖逖大營,箭矢如雨,火光沖天。
祖逖親自披甲持劍,在亂軍中穩住陣腳,最危急的時刻,蓬陂塢主陳川派來了援兵。
當李頭率領的生力軍加入戰局時,祖逖看到了希望,這些中原豪強並非鐵板一塊,他們心中還藏著對晉室的最後一絲期待。
人心,才是北伐最稀缺的糧草。
隨後的戰事如同奇蹟,祖逖以少勝多,智取譙城,石勒派石虎率五萬大軍來攻,竟被擊退。
最令人稱奇的是,這位出身豪族的將軍,竟能讓互相攻伐的塢堡主們放下仇怨。
趙固、李矩、郭默這些桀驁不馴的地方武裝,紛紛接受他的號令。
在黃河以南,一個以祖逖為核心的抗胡聯盟正在成型,這是八王之亂後,晉室旗幟第一次重新插滿中原。
「聞雞起舞」這個勵志故事想必大家都聽過。
祖逖和劉琨,兩位少年英雄,半夜聞雞鳴即起身練劍,立志報國。
他們的勤奮被傳頌千年,成為激勵後人的典範。
可歷史的真相往往殘酷,老師不會告訴你,這兩位英雄的結局,或許淒涼的讓人難以想像。
他們經歷了什麼?又為何會有慘痛下場?
少年壯志、亂世伏筆
洛陽司州主簿的官署內,祖逖和劉琨這對摯友,又一次抵足而談,直至深夜。
他們的話題從詩書禮樂到天下大勢,從朝堂詭譎到邊疆烽火,言語間儘是少年人的熱血抱負。
他們並不知道,多年後,這段在洛陽的歲月會成為「聞雞起舞」的傳奇,而他們的命運,也將隨著這個搖搖欲墜的王朝一同沉浮。
那時的西晉,表面仍維持著大一統的繁華,內里卻早已危機四伏。
晉惠帝司馬衷痴愚無能,朝政被皇后賈南風一手操控,而各地藩王虎視眈眈,暗流涌動。
更可怕的是,北方胡人部落趁著朝廷內鬥,不斷南下侵擾,邊境烽煙四起。
祖逖出身范陽豪族,自幼不拘小節,輕財重義,常散盡家財接濟貧苦鄉鄰。
他的身上既有豪俠的慷慨,又有士人的抱負。
劉琨則來自中山劉氏,風姿俊朗,文采斐然,二十歲時便以文章名動洛陽,被譽為「洛中奕奕,慶孫越石」。
兩人性格迥異,卻因共同的志向成為莫逆之交。
他們不甘心只做案牘勞形的小吏,而是渴望在亂世中力挽狂瀾,哪怕前路荊棘密布。
某個凌晨,天尚未亮,一聲雞鳴劃破寂靜。
祖逖猛然驚醒,推醒身旁的劉琨。
劉琨睡眼惺忪,喃喃道:「此時雞鳴,恐非吉兆。」
祖逖卻目光炯炯,朗聲道:「此非惡聲也!天下將亂,正是男兒奮發之時,豈能虛度光陰?」
說罷,他翻身下榻,拔劍出鞘,在月光下揮灑起來。
劉琨見狀,胸中豪氣頓生,亦提劍相隨。
這一刻,雞鳴不再只是尋常的晨號,而成了他們生命中一道無形的戰鼓,催促著他們向未知的命運進發。
但現實遠比理想殘酷,洛陽的朝堂上,賈南風專權跋扈,誅殺太子,引發諸王不滿。
邊疆的胡人部落蠢蠢欲動,而朝廷卻無暇顧及。
江統曾上書《徙戎論》,警告朝廷若不驅逐內遷胡人,必成大患,可他的諫言如石沉大海。
大廈將傾,獨木難支,祖逖與劉琨的滿腔熱血,在時代的洪流面前,顯得如此渺小。
他們仍在等待機會。
歷史從不缺少英雄,但英雄的結局,往往由時代書寫。
不管未來怎樣,但此刻,他們只是兩個心懷壯志的年輕人,在雞鳴聲中,迎向屬於自己的黎明。
八王之亂
起初,祖逖對齊王司馬冏寄予厚望。
這位年輕的藩王素有賢名,入主洛陽後廣納賢才,似乎真有重振朝綱的魄力。
祖逖被徵召為大司馬掾,每日埋首案牘,起草文書,試圖在混亂中維持一絲秩序。
可好景不長,司馬冏很快沉溺權欲,驕縱跋扈,最終被長沙王司馬乂所殺。
理想尚未展開,便已破滅,祖逖第一次嘗到了政治幻滅的苦澀。
與此同時,劉琨的處境同樣艱難。
他輾轉於諸王之間,憑藉過人的才略漸露頭角,可每一次站隊都如同刀尖行走。
八王混戰,今日的盟友可能就是明日的仇敵,忠誠成了最廉價的籌碼。
在這片權力的焦土上,道德和理想被碾得粉碎,活下來的法則只剩下審時度勢與冷酷算計。
最令祖逖心寒的,是東海王司馬越的崛起。
這位權臣打著匡扶晉室的旗號,卻將晉惠帝當作傀儡,肆意弄權。
祖逖曾短暫效力於他,可很快就發現,所謂的"忠君"不過是司馬越野心的遮羞布。
當司馬越將皇帝劫持至長安,自己獨攬朝政時,祖逖徹底失望了。
他原以為能在這亂世中尋得明主,可兜兜轉轉,發現自己效忠的不過是一群精緻的利己主義者。
北方的戰火越燒越旺。
匈奴人劉淵在并州自立為王,羯族首領石勒縱橫河北,而朝廷的精銳卻在諸王的內鬥中消耗殆盡。
劉琨被派往并州任刺史,名義上是鎮守邊疆,實則是被丟進了一片死地。
當他帶著千餘殘兵抵達晉陽時,眼前的景象令人絕望,城牆殘破,屍骸遍野,胡騎在城外游弋,而朝廷的援軍遙遙無期。
這是一座被遺忘的孤城,也是一塊試煉英雄的磨刀石。
令人驚嘆的是,劉琨硬是在這片廢墟上創造了奇蹟。
他安撫流民,重建城防,甚至用胡笳聲勾起匈奴士兵的鄉愁,瓦解敵軍的鬥志。
短短一年間,晉陽竟重現生機,成為北方抗胡的重要據點。
可就在形勢稍有好轉時,內部的傾軋又給了劉琨致命一擊。
他信任的部下相互攻訐,鮮卑盟友反覆無常,而遠在建康的朝廷除了空頭封賞,給不了任何實質支持。
個人的才能終究敵不過體制的腐朽,英雄的孤獨,在這一刻顯得格外刺目。
當劉琨在晉陽苦苦支撐時,祖逖選擇了另一條路。
母親去世後,他借守孝之名遠離朝堂,冷眼旁觀這場權力的狂歡。
311年,洛陽陷落,匈奴人縱兵屠城的消息傳來,他終於下定決心,帶著數百族人南渡淮河,投奔琅琊王司馬睿。
這是逃避,也是新的開始,在南方的煙雨樓台中,一個更宏大的計劃正在他心中醞釀。
亂世中的選擇,往往無關對錯,只關乎生存信念。
祖逖南下,劉琨北上,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,卻同樣荊棘叢生。
英雄的絕唱
建康城司馬睿的王府內,祖逖站在殿中,言辭懇切,目光如炬。
他剛剛向這位琅琊王陳述了北伐的計劃,描繪著收復中原的藍圖。
司馬睿微微頷首,臉上掛著禮節性的讚許,可眼神卻飄向了窗外。
祖逖沒有說破,但他心裡清楚,這位未來的東晉開國之君,關心的從來不是北方的遺民,而是江南的安穩。
朝廷的"支持"寒酸得令人心酸,一千人的糧餉,三千匹布帛,沒有一兵一卒。
但祖逖接下了這道幾乎等於放逐的任命。
313年秋,他帶著百餘親族部曲在京口渡江。
船至中流,江風獵獵,祖逖突然起身,以槳擊水,朗聲道:
"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,有如大江!"
這誓言如金石墜地,在歷史的迴音壁上震盪千年,可當時在場的部曲們,只聽見了風中隱約的嘆息。
北伐的開端比想像中艱難,中原歷經戰亂,早已是塢堡林立,豪強割據的局面。
祖逖的使者殷乂因出言不遜被張平所殺,第一次交鋒就見了血。
在中原的廢墟上,沒有王師的榮耀,只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。
轉折發生在一次夜襲。樊雅率死士突襲祖逖大營,箭矢如雨,火光沖天。
祖逖親自披甲持劍,在亂軍中穩住陣腳,最危急的時刻,蓬陂塢主陳川派來了援兵。
當李頭率領的生力軍加入戰局時,祖逖看到了希望,這些中原豪強並非鐵板一塊,他們心中還藏著對晉室的最後一絲期待。
人心,才是北伐最稀缺的糧草。
隨後的戰事如同奇蹟,祖逖以少勝多,智取譙城,石勒派石虎率五萬大軍來攻,竟被擊退。
最令人稱奇的是,這位出身豪族的將軍,竟能讓互相攻伐的塢堡主們放下仇怨。
趙固、李矩、郭默這些桀驁不馴的地方武裝,紛紛接受他的號令。
在黃河以南,一個以祖逖為核心的抗胡聯盟正在成型,這是八王之亂後,晉室旗幟第一次重新插滿中原。
 呂純弘 • 11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
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
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