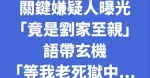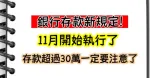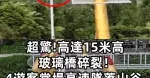2/5
下一頁
她,逃亡17年,後被尊為「國母」,48歲自願離婚,86歲終老澳門

2/5
2月,孫中山讓盧慕貞帶著孫母從澳門前往南京,政府安排了官員接待,有人建議她學幾句英文,好應酬外國來賓。
她沉默良久,只說:「我不懂那套。」第二天,她從南京西門的布市買了些布料和縫紉針,就在大總統府的小房裡縫衣做飯,她的「國母」生活,只比舊時村婦多了一身黑呢大褂。
孫中山那時忙於視察全國交通路政,從滬寧鐵路到四川巴蜀,幾乎不著家,盧慕貞跟隨一次。
途中多是商會接待、外國工程師陪同,滿桌西餐、紅酒,她完全插不上話。第二天一早,她找人轉交給孫中山一句話:「我想回鄉養老。」
孫中山沒有阻攔,只是讓人送她回澳門。
她不是革命的同路人,更不是政治的合作者,她只是「先生的妻子」。
1913年,孫中山再度起事,失敗後流亡日本,盧慕貞再次帶著孫母從澳門避走,幾次險些被截。
那時「國母」的稱號仍印在教科書和宣傳冊上,她住在租來的小屋內,門外貼著一個福字,裡面是她縫的棉襖和熬的藥湯。她說:「國母之名,虛有其表。」
有人問她:「你怨過他嗎?」
她沒回答,只是盯著爐子發獃,爐灰里,埋著她寫的一封信,寫了又撕,撕了又埋,沒人知道內容,只知道她那時經常半夜咳嗽,一口氣咳完,翻身繼續睡。
她曾站在歷史的門檻上,可她的腳是三寸金蓮,踏不進去。
45歲離婚——成全革命的「可」字
1912年,孫中山在日本橫濱,那一年,他身邊多了一位年輕女子:宋慶齡,她畢業於美國威斯理學院,英文流利、思維活躍,常為孫中山翻譯文件、起草文電。
他們常常徹夜長談,話題從鐵路、法制談到基督、國家。
她沉默良久,只說:「我不懂那套。」第二天,她從南京西門的布市買了些布料和縫紉針,就在大總統府的小房裡縫衣做飯,她的「國母」生活,只比舊時村婦多了一身黑呢大褂。
孫中山那時忙於視察全國交通路政,從滬寧鐵路到四川巴蜀,幾乎不著家,盧慕貞跟隨一次。
途中多是商會接待、外國工程師陪同,滿桌西餐、紅酒,她完全插不上話。第二天一早,她找人轉交給孫中山一句話:「我想回鄉養老。」
孫中山沒有阻攔,只是讓人送她回澳門。
她不是革命的同路人,更不是政治的合作者,她只是「先生的妻子」。
1913年,孫中山再度起事,失敗後流亡日本,盧慕貞再次帶著孫母從澳門避走,幾次險些被截。
那時「國母」的稱號仍印在教科書和宣傳冊上,她住在租來的小屋內,門外貼著一個福字,裡面是她縫的棉襖和熬的藥湯。她說:「國母之名,虛有其表。」
有人問她:「你怨過他嗎?」
她沒回答,只是盯著爐子發獃,爐灰里,埋著她寫的一封信,寫了又撕,撕了又埋,沒人知道內容,只知道她那時經常半夜咳嗽,一口氣咳完,翻身繼續睡。
她曾站在歷史的門檻上,可她的腳是三寸金蓮,踏不進去。
45歲離婚——成全革命的「可」字
1912年,孫中山在日本橫濱,那一年,他身邊多了一位年輕女子:宋慶齡,她畢業於美國威斯理學院,英文流利、思維活躍,常為孫中山翻譯文件、起草文電。
他們常常徹夜長談,話題從鐵路、法制談到基督、國家。
 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